元青白瓷印一个王朝特殊的产物
图文选自《金石研究》第二辑,文字内容有删减,原标题为“元青白瓷押印考”。本文所用图片是近期出土的一批元代青瓷押印,在此向作者表示感谢!
押,即花书,是姓名的符号化,似文字,亦似图案,有仅一汉字者,也有单字与花书有机结合的,融为一体,极富变化之美。周密《癸辛杂识》载:“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南北朝时期,署押又被称为“画敕”“花字”“花书”等。唐宋以来,文书用押署越来越频繁,据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中记载:“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草书,唯名不得草,遂以草名为‘花押’。”“押”实际上是一种署书的样式,与今人的署名签字功能略同。花押印基本都用朱文,形式不一,有长方形、方形、圆形、葫芦形等。现传世最多的是元代的花押印,称之为“元押”。上面一般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也有单字楷书或是篆书。押印为何会盛行于元代,《南村辍耕录》中云:“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故此应该是元代使用押印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并且传世的花押印材质大多为铜质、玉、石质等。近日,笔者对近期出土的一批元代青瓷押印分别从基本形制与分类、文字与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考据,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这批青瓷押印外形及使用情况看,印钮虽有部分完整,但大都印钮残缺,或是钮倒粘连在印背。而印钮粘接并非在印台中间位置,也并未见有使用过的痕迹,故疑为这批瓷押印应该是当时的残次品,也就是行家们所说的“窑址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叶”押,此印为压模法制作,钮倒粘连于印台,“叶”字下方较窄,而中间较宽,有种朴拙之气。
“李”押,此方押钮残,为压模法制作,但未上釉,且“李”字结构为上大下小。
“姚”押,此方印与前三方有所不同,为刻制法制作,字口深凹,刀法纯熟,钮倒粘连于印台。
“方”押,“方”字的撇划与横折钩相交叉,为压模法制作,从钮残的痕迹来看,钮并未在印台中间位置。
“夏”押,“夏”字的捺划带有隶书笔意,印面为压模法制作,钮倒粘连于印台。
“项”押,无钮,也未见到有钮残的痕迹,可以证明当时制作时未粘钮,挂粙极为不均,压模法制作,印边有残。
“廖”押,“廖”字笔划方折,如魏碑笔意,钮残且痕迹偏离印台,压模法制作。
“邵”押,压模法制作,钮倒粘连于印背,且已断为三角形钮,印面弯曲变形严重。
“蒋”押,“蒋”字带有明显的篆隶笔意,钮残,但其釉色极为美观,压模法制作。
“合同”押,为正方形,阳文两字上下竖式,“合”字结构上面的“人”形,笔划作平直处理,“合”字将“同”包容在内,篆书入印且刀痕清晰,疑为刻制法制作。
葫芦形“合同”押,钮残,从钮残的痕迹上看,钮并非在印背中间位置,压模法制作。
“合同合同”押 ,两印在烧制时粘连在一起,印面刀痕清晰,疑为刻制法制作。
鹿形押有两方,第一方,钮残,且钮斜倒粘连于印台,其图形中将鹿角与身上的斑点表现得极为形象。第二方,钮完好,这两方押印均系压模法制作。
另有葫芦形“平安”押,钮残,但釉色均匀柔美。钟形如“吉”押,钮残,为压模法制作。鼎形“可齐”押,钮残,为压模法制作。
如“福”押,方形,篆书入印,其中“福”字中“田”作“□”,钮残,印边残,疑为刻制法制作。
再如“印”押,钮残而粘连在印背,刀痕清晰,有宋印之风格,为刻制法制作,但印面变形。
还有“□”押,方形白文押印,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押印大多都为阳文,此种白文押印极为罕见,白文线条末端留有明显的刀痕,疑为刻制法制作。
“堇圭”押,银锭形,“谨”作“堇”,“封”作“圭”,压模法,钮完整,束腰银锭形印面。
在印面内容及字体方面,大致可分为楷书和篆书,其中姓氏押基本上都是楷书加一“押”字,而且印面基本都为长方形,亦有方形。同时,在对比中发现,凡压模法制作的押印,边框与印文线条相当,特别是刻制法制作的押印,印边略粗于印文线条。其中的姓氏押文字一般在框内直接安排,图像押却是先在框内安排图形,然后在物体图形内安排文字,甚至有的文字根据图形进行夸张变形,这些文字与内容方面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用于书信、合同类的画押中,印文基本上用篆书。但凡入印的楷书文字则书写规范,书体中有篆隶笔意,未见有错字和缺少笔划的现象。“合同”一词,在《周礼·秋官·朝士》中记载为“判书”。在《疏》中则为:“云判。半分而合者,即质剂传别分支合同,两家各得其一者也。”《通俗编·货财·合同》中记载:“按今人产业,多于契背上作一手大字,而与中央破之,谓之合同文契。”通过“合同押印”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合同押印应是官私并存使用的。
2、另一种就是姓氏押印印内多为一楷字加一押字,其文字与线条未见有和边框交接或粘连的现象,这正符合元押的基本风格。但配在姓氏下的画押图形,基本上失去了元铜押印用笔的圆转和缠绕的规律,而是采用原来的图形,在结构上进行了方块化处理。尤其是在线条方面用方折代替了圆转,并且对画押的图形进行了“楷书化”处理。故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使印面形式与文字和谐统一。如“胡”押、“姚”押、“李”押、“罗”押、“雷”押、“何”押等印。
3、这批元瓷押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篆书字体,印文中有的篆字出现了删减笔划或符号化的情况。如封缄类押印“堇(谨)圭(封)”:“谨”从“堇”,“封”从“圭”;“堇”作“□”;“圭”作“□”。如“福”押:田作“□”。“平安”押:“平”作“□”。并且有些笔划已成了这个时期写手约定俗成的写体,成为一种专用符号,这应该跟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俗有关。因为楷书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通用文字,篆书已经逐渐退出社会通用文字地位,成为装饰性文字,所以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注重押印的实用,并不注重文化等内涵。
4、从这批瓷图像押印看,与元铜押印基本类似,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及稍后的汉代就有专门的图像印,图像多表现为动物等图案,且图像简练精致极富艺术趣味。后历代亦有图像印,但艺术风格较春秋战国和汉代则逊色很多。元代图像押印大盛,五花八门,有动物、人物,身着官服的官吏形象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器物等。这批元青瓷押印中的图像押印为朱形白底。图像中糅进了文字、汉楷,亦有图像中杂以花押,更具实用性。
成吉思汗创建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由非汉族主政的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各民族统一在中央政权统治下,具有充裕的劳动力和物力。手工业、商业发展之快,远超辽、西夏、金时期。百业繁盛,无不见押印戳记的行用。从这一批存世的青瓷押印的制作工艺来看,第一种采用压模法制作,第二种则是直接在瓷坯上刻制而成。而从这批瓷押印形制及质量来看,因瓷印烧制成功率极低,印坯经烧制后平整度及尺寸与烧制前均有明显差异,其中有部分出现弯曲变形、四周翘起、中间鼓出、印印粘连等,这些方面都足以说明瓷押在烧制时并不是单印烧制,而是同样印文一次做数枚同时烧制。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元代官方和民间签定合约及买卖契约时几乎未见有使用瓷押印的情况,而以铜押印居多。所以,此次出现如此众多的瓷押印,无论是从这批瓷押的印面布局及文字线条来看,还是从制作工艺来看,都显得十分精美而又古朴,这对我们研究认识元代押印制作工艺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史学价值。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元代,元押艺术是这个王朝的产物,并且盛行于世。而这一批青瓷押印的出现,无论是从形质、印面及制作工艺,还是从单独的艺术价值来讲,它给我们呈现出一种疏散拙朴、苍古浑厚、线条劲健、文字端庄、秀美流丽的艺术气象,也为我们欣赏和学习提供了宝贵而难得的实例。当我们在欣赏的同时,对这批青瓷押印的思考与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它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在整个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这种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去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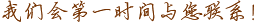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